免疫新例量替雷利珠单抗联合靶向治疗成功缩
2022-7-1 来源:本站原创 浏览次数:次原发性肝癌主要包括肝细胞癌(HCC)、肝内胆管癌和肝细胞癌-胆管细胞癌混合型等不同病理类型,HCC占所有病理类型的70%~90%,是人类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居于癌症相关死亡原因的第三位[1-3]。目前,针对HCC的治疗不再局限于传统方法,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等系统治疗在HCC的治疗中相互补充,为HCC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4]。本期为读者分享一例初诊伴肝右静脉及下腔静脉癌栓的肝细胞癌患者诊疗经过,患者经系统治疗后,成功手术获pCR疗效,术后持续随访至今18个月无复发征象。(病例点评专家:邱双健教授;病例分享专家:易勇副教授。)
邱双健教授复旦大学博士生导师
医院肝肿瘤外科常务副主任
国家肿瘤质控中心(国家癌症中心)肝癌质控专家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
上海市肝病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上海市免疫学会理事兼肿瘤免疫专委会副主委
长期从事肝脏外科、肝移植工作,入选上海市优秀学术带头人计划,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国家级及省部级课题多项。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两项、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等多项奖励。
易勇副教授
复旦大学外科学博士
医院肝外科副主任医师、科室教学秘书
上海市肝病学会肝肿瘤学组委员
主要从事肝癌复发转移的基础与临床工作。擅长肝癌微创外科(腹腔镜)治疗,有两千例肝切除主刀经验,对复杂肝癌、肝门胆管癌切除、晚期肝癌转化治疗等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主要研究方向为微环境与肝癌转移复发、肝癌转化治疗研究,负责两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含共同)在JournalofHepatology等杂志发表SCI论文二十余篇。入选年度上海市教委晨光计划及年度上海市优秀青年专科医师培养资助计划。
基本情况
一般资料:患者男性,64岁,于年5月21日入院。
主诉:体检发现肝占位伴甲胎蛋白(AFP)升高4天。
既往史、个人史/家族史:无特殊。
乙肝:HBsAg(+),HBeAg(+),HBeAb(+),HBV-DNA:2.53×10^2。
肝功能:AST22U/L,ALT11U/L,Alb41g/L,TB13.4μmol/L。
肿瘤标志物:AFP.0ng/mL,CEA3.6ng/mL,CA19-9:22.0U/mL,DCPmAU/mL。
腹部MRI(年5月25日):(如图1所示)肝右叶HCC伴门脉右后支受侵犯,肝右静脉、下腔静脉癌栓;肝硬化,双肾囊肿。肝右叶实质的弹性硬度测值平均为12.8kPa。检查肝右后叶肿瘤,伴肝右静脉及下腔静脉癌栓形成,手术切除相对困难。
图1治疗基线腹部MRI
诊断:肝细胞癌伴肝右静脉及下腔静脉癌栓(BCLC分期C期;CNLC分期Ⅲa期)。
治疗经过
第一阶段:术前治疗(免疫+靶向)
治疗方案:患者于年5月28日至年8月19日期间共接受4周期靶免联合治疗,方案为替雷利珠单抗mgq3w+仑伐替尼12mg口服qd,无明显治疗相关不良反应;用药期间AFP变化如图2所示。
图2用药期间AFP变化
影像学及疗效评价:4周期用药后(年8月19日)MRI示肝右叶恶性肿瘤治疗后,病灶基本坏死,门脉右后支受侵犯,肝右静脉、下腔静脉癌栓,总体较年7月30日片相仿;肝硬化,脾肿大;双肾囊肿。治疗期间动态变化如图3所示。
图3左、右分别为第2、第6周期治疗后影像学表现
第二阶段:手术治疗
治疗方案:患者于年8月25日行肝右后叶切除术〔特殊肝段切除术(Ⅵ、Ⅶ段)〕+下腔静脉取栓术+膈肌部分切除术+膈肌修补术。
图4术中所见
术后病理诊断:未见残留癌细胞,符合治疗后改变。
疗效评价:pCR。
第三阶段:术后治疗(免疫+靶向)
治疗方案:原方案(仑伐替尼+替雷利珠单抗)维持治疗至年7月18日,总疗程为1年。
安全性评价:蛋白尿++(AE2级),考虑与仑伐替尼相关,予仑伐替尼减量。
术后情况:术后定期复查,末次随访(年1月13日)超声:肝右叶手术区积液伴机化,脾大。术后OS/DFS:18个月。
病例总结
本例患者老年男性,因“体检发现肝占位伴AFP升高”就诊,结合症状、体征及辅助检查结果,诊断为肝细胞癌伴肝右静脉及下腔静脉癌栓,手术切除相对困难,故先予以免疫(替雷利珠单抗)联合靶向(仑伐替尼)治疗4个周期后,病灶基本坏死,再行手术治疗,术后评价疗效达pCR。术后仍采用原方案维持治疗,定期复查,截至末次随访(年1月13日),无肿瘤复发征象,术后OS/DFS至今18个月。
专家点评
HCC是第5大常见肿瘤,由于早期诊断不及时、疾病进展速度快,导致肿瘤可切除率低[4];即便能够进行根治性切除的患者,其5年复发率也高达80%,5年生存率仅为18%[5],本例患者在确诊时已是HCC晚期,不适宜直接接受手术治疗。如何提高患者肿瘤的可切除率、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是临床亟待解决的问题。对于中晚期无法直接进行手术切除的肝癌患者,单独使用免疫或靶向药物的疗效都比较有限,且肿瘤容易产生耐药性,两者联合作为肿瘤治疗的“新势力”受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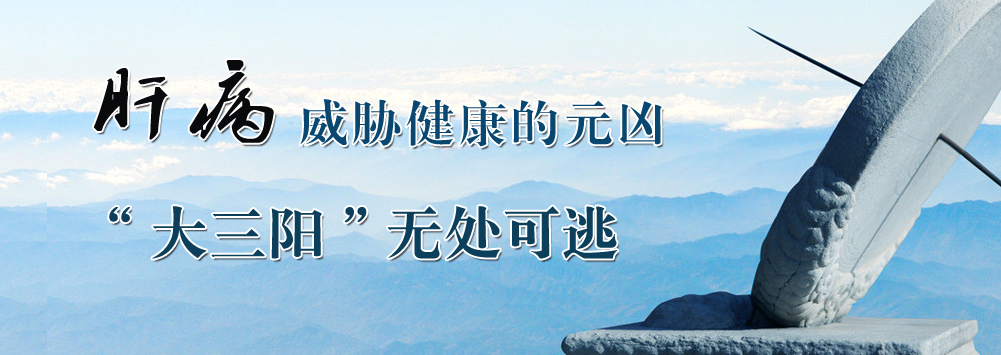
 健康热线:
健康热线: